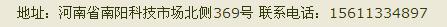参与者说去过一次还想再去是什么体验
可能到了巴厘岛却没有去海滩的人少之又少,而我就是其中一个。
可能到了巴厘岛却住在小山村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个。
巨大的芭蕉叶,从头顶垂下的藤蔓,脚边淙淙的小溪流水…在这里遇见的小伙伴们、小孩子们、住家的uncle和mama…是我对这里的记忆。
(和晓莹以及友善的司机大哥)
到达登巴萨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小伙伴晓莹。俩人一起租车去看了巴厘岛的梯田,占山为王的猴子,倒挂在树枝上的蝙蝠,只有海水退潮才能见到台阶的水神庙。
第二天和大部队集合后我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志愿活动。
其实我们这项活动算是边做志愿边旅行。我们一起去过泥泞的森林,玩过梯田里巨大的秋千,看到过寺庙里虔诚的信徒,品尝过二十多种特色咖啡和茶,画过鸡蛋花,做过向神明表达感激之情的贡品,学过当地的舞蹈…当然还有许多我们平时自己溜达、聊天时候经历的种种。
我们晚上一起备课,分小组讨论怎么教小朋友,准备什么歌曲和游戏,让两个小时不那么无聊。在当老师方面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只能说是努力用心和小朋友们玩在一起、学在一起吧。
下面我不想只是记录日常,
我想写下这个地方给我的感受。
走在山林里时,我脑中一直盘旋着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这山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它们,像是当地人从大自然肆意生长的某一条缝隙中寻出来的。这个山林不是景点,只是这个村落后面的一座山。当我走在深深沉在泥里的石头“路”上(其实就是顺着地势码成一列的平整的石头,大部分路还没有这石头“路”),看到小溪上面三根竹子捆在一起做成的桥、偶然出现的小木屋、某处地里整齐的水稻,才感受到前人修饰的痕迹。
(过竹桥)
布满青苔的台阶,延伸到了山林入口处的水潭,就不再出现了。看到水潭这里的一瞬间,我只想用一句很俗的话来形容:像仙境一样诶!巨大的古树矗立在一旁,茂密的枝叶间垂荡下条条藤蔓。树干上肆意地爬满苔藓,树根突出地面。通往水潭的台阶是断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近它,只能远远地望着漂浮在水面上那一朵朵盛开的莲花。水潭围栏上有着不同的佛雕。我总觉得这里会突然出现特别智慧的猴子长老,给迷途的人点拨人生的奥妙。
(台阶结束的地方望向山林里)
在树林里走着走着,我和晓莹还有小伙伴Sonia就落到里队伍最后,和我们的当地小向导一起垫底。
和工作人员在一起走的好处就是:能走更泥的路,看更美的风景,得到更多小惊喜还有黑照。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觉得这里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可以说是很浪漫的感觉(也可能是我见识不多,所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可爱)。
当时我们一起走着走着,工作人员看见了小溪旁岩壁上的小红果,他叫我们一起看,我们都觉得很可爱。然后他立刻决定淌水摘给我们。还好溪水不深,他又习惯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探脚下去,站在溪水中轻轻摘下了岩壁上的几颗小红果给我们;我们教的小女孩们每天上课前都去采花,每见到我们中的一个,就选出一朵别在我们的耳畔,只可惜每人只有两只耳朵,所以上课前大家手里都有一捧花;在树林中,晓莹看着巨大的叶子心动想要一片,但我们不敢随便摘(不敢随便采花采草嘛),其实也是没足够力气拔断它粗壮的茎。工作人员知道后,帮我们一人摘了一片足以当帽子的绿叶。
(晓莹和我俩的叶子)
我记得很深,这种借自然之物不经意间流露的温情。
他们采下一片叶子一朵花时,我并没有觉得是对自然的破坏。这种感觉不同于我们平时在路边或是景区随手折下好看的花好看的叶,也不同于刻意在花店中买下一捧昂贵的花束。
花花草草在这里不是人的附庸,人的安排。你不需要立牌子“请勿摘花”,因为人们根本不会想去阻碍它们茂盛的姿态。你也不需要培养出超常发挥的优良品种,因为它们已经足够高大漂亮;你不用去规划它们的生长的路线、形成的图案,它们总会有自己的方式恰到好处的组合在一起…
它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山林里不可思议的美景)
有一次我们在下雨的路上看到一位老人。她手举着一片巨大的芭蕉叶挡雨。这感觉就像是向自己的好朋友借了一把伞。
人与自然,谦逊和爱。
也许你会说,这里的植物长的好是气候原因,才包裹住了整个村落,因此才有这种感觉。
但我想提我们学做的贡品。贡品,是为了表达对神明的感激,它全是用植物做成的。新鲜的香蕉树叶做成小盒子,至少四种花按同一方向放在里面,摆放在家门口的地方。开始我以为只有村子里还保留这种习惯,但后来晓莹提起来,我们第一天租车的司机在车里也放了这样的贡品。
(我们一起做学做贡品图片:Sonia)
我不懂他们的宗教,甚至不知道他们信仰的教的名字,更不太明白到底为什么要放花作为贡品。但我猜是因为感激自然的馈赠吧。把神明赐予的美好事物再献予神明,来表达心中对于美好的认同和感恩。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哈哈哈。
但我觉得这份心意足以表明他们对于大自然的爱意和敬意。就像他们摘下花送给我们,应该只是想分享这份美丽。采下一朵花不是因为我想拥有,而是因为我很欣赏。人的存在并没有让美丽的自然风光沦为一个背景色,或是人类的附庸品。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人是慢的,周遭的环境是快的。坐在台阶上看着天上的云,闭上眼听噼噼啪啪敲打地面的雨。云跑的很快,时时刻刻在变,雨说下就下,根本不是天气预报能报的。
对于此行看巴厘岛庞里小村的自然环境,加上衍生出来的感受就先写到这里吧,再写一写对这里人的感受吧。
出去不止是看风景,更多的可能是遇到人。
和晓莹去梯田的那天不能更幸运(虽然我们去的不是最有名的那个)!我们到达那片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当地人带着牛在里面耕地。牛儿在没小腿肚的泥地里慢慢走,里面的人却在疯狂的跑哈哈哈。他们丝毫不介意从头发到脚趾都是棕灰色的泥,开心地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男人们男孩们在泥里赛跑,被下面松软的土地陷住脚绊倒,就一起坐在泥里哈哈大笑。有一个一直没进到泥里的伙伴被他们招呼。他终于下去。刚一站稳,就被几个男人笑着猛拉进去,跌坐泥潭,一下子从头到脚变成棕色。他无奈地和他们一起大笑,然后在里面跑起来。
(耕作的人们)
我和晓莹因为根本没有带可换的衣服,不敢像他们一样躺里面…但我们觉得机不可失啊!
我们两个下定决心后,把包交给司机大叔,鞋一脱袜子,赤着脚进了泥里。当地人看我们进了泥,都特热情的欢呼,然后问我们是哪里来的。他们中有人听我们说是China,立刻用印尼腔说“你好”“恭喜发财”之类的哈哈哈。一个“泥”大叔还走过来,连指带笔画的邀请我们一起合影。大人们也示意他们的孩子们不要在泥里飞奔了,免得溅我俩一身泥。加入他们最淳朴的耕种活动,好像他们也觉得我们很勇敢,也是对他们文化的尊重和认可。毕竟不是所有外乡人都愿意脱了鞋子袜子,被甩到脸上、衣服上、手机上都是泥点子。他们一直问我们开不开心,感觉怎么样,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个像是村长或是乡绅一样的绿衣大叔,英语特别好,很热心的给我们介绍他们这里。
(和当地超友好的大叔们照相)
等我们洗干净脚重新出发的时候,发现刚刚在山泉水下冲洗过的小孩子,又都在河里坐着玩。他们就在里面边洗边玩。看我们从旁边走过,抬起头来和我们大声的说“Hello!”
(在小溪里洗澡,照片来自小莹)
在巴厘岛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英文单词可能就是“hello”。尤其是在后来的小村子里,走在路上村民们就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
这就是我对这里人的第一感觉:热情。
对他们的第二个感觉是:纯粹。
到村子里的第一个下午,工作人员我们逛村子。我们路过一堆堆沙石,旁边站着一溜的女人。她们有小孩有老人,人人头顶一个筐,用来装这些沙子搬去院子里。工作人员跟我们说,村子里的人都是互相帮助盖房子的。他们彼此之间不图利益,全都是自发的来帮这家人盖房子。探头看进去,院子里是男人在做重活。
我真的挺震撼的。之前路过过一家在装修房顶,我还想,他们这个村子里是哪找的工人啊?
没想答案是这样的。
(排着队装沙石的女人们)
再后来,我们遇到了这里的小孩子。
“Myhobbyisfootball!Iwanttobeafootballplayer!”自我介绍时,男孩子们用不利索的英文这样喊着。
他们每天中午都在一起赤着脚踢一个没气的甚至破洞的皮球。小男孩们用集会时的空地,大男孩们用有球门的水泥地足球场。有一天音乐组的小伙伴们特意选了wewillrockyou这首歌,给这帮爱踢球的小男孩们。他们本来听到这首歌没什么反应,在知道这首歌用于世界杯主题曲,每次都扯着脖子跟喊那句“wewillwewill,rockyou”。
对他们来说,踢足球是每天下午相见的小伙伴,是没气的皮球,是随便哪里的一片空地,是飞奔生风的一双赤脚。
看着他们干净纯粹的双眼,上蹿下跳的身影,我常常想,他们未来会走向哪里。村子里其实老人和小孩居多,就像我们的很多村庄一样,青壮年都去大城市发展了。
(以上照片来自sonia和小莹)
我们住的mama家里,挂着大幅的她女儿大学毕业时的全家福。uncle家把小儿子的大学学生证都挂在墙上。和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一样,年轻人们都把脚步迈向城市。父母也的确很以他们为荣。
这里的生活和城市那么的不一样。
家门口放着鲜花做的贡品,公鸡母鸡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蹦跳,小狗大狗懒洋洋的躺在路中央,老牛们不紧不慢地吃着槽子里的草…
(牛大哥你好啊)
我没有资格说他们应当像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样,回到家乡,保护传统风貌。毕竟我就在今天还坐着高铁,四个多小时就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上海,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成果。
刚刚离开巴厘岛的几天时,我思考起这个问题,觉得他们应当会想念家中的绿水青山,惦念着漏气的皮球,想回到家乡。
但我现在对我的这种想法产生了怀疑。
我想起前两天读完的《白鹿原》里的一个片段。白孝文在城里过的不错之后,希望回到家乡向父亲道歉并且祭祖。他回来时风风光光,看到村口的古树,家里的房子,也触景生情。但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大公鸡,现在更希望跳上墙头跃上柴禾垛引颈鸣唱。看着曾经带来幸福与痛苦的地方,产生了有点像公鸡对于蛋壳的感情。当他临走,望向原上,冷不丁说了一句:“谁走不出这原谁没出息。”太太温存地一笑:“可你还是想回来。”白孝文说:“回来是另一码事!”
这本书我只刚读过一遍,对于这些情节把握的也不一定准确。但我觉得,虽然国别不同,时代不同,但人心可能是相同的。长期离开村子的孩子们对家乡的感觉,可能就像是大公鸡对蛋壳的感情吧。
不过呢,先不用急着想那么远的事情,而且我也没什么发言权,毕竟我是个局外人,只能猜测他们将来的心理,很多时候我的猜测还会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我觉得就现在而言,这些小朋友们澄澈的双眼需要去看看高楼大厦,去看看华丽的城市,去看场足球盛典,也需要去看看被过度砍伐的植被和城市肮脏的角落。他们确确实实需要走出去。
和他们相处以及后来回顾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这些孩子就是普普通通的小孩子。他们的天真烂漫,或者是调皮捣蛋,甚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都与我曾经见到的那些孩子无异,与我无异。只是我们后来受到的教育,见到的东西不一样,让我们变得不一样了。
我这些感悟的确都是大家平时就在说的话。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差异。
但我觉得自己体会到,和仅仅是听到,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冲击力的。
神明赐予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不受束缚的童年。他们不用攀比鞋子,因为他们赤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
但没有谁能一辈子躲在神的翅膀下。我有时会想,他们某一天也许就是坐在田垄上看夕阳的农民,是机场到处搭话的出租车司机,是漫天要价的商贩,也可能是走出国门的医生、教师、建筑师…他们见过的雨再美,星星再亮,也应当见见枫叶红、雪花飘。
记得一天晚上,天上没有云。我们仰着头望着璀璨的星空。明亮的银河弯着绵延向远方。
*图文来自出走世界巴厘岛·庞里项目参与者火龙果快递员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zhaigou365.net/fzff/131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