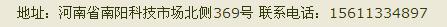刘恒向无声的草木致敬,向平凡的自己致敬
点击上方“文艺报”,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草木是个路标,一头指向了空间,在庞大混沌的空间里面,最清晰也最亲切的一个小地方名叫故乡。
另一头指向时间,在凌乱不堪的时间碎片里,最难忘的是自家生命的刻度——那些被春夏秋冬埋葬了的平凡的日子。
评论
向无声的草木致敬
刘恒
文
我认识董华30多年了。他是个厚道人,以前是,现在还是。《草木知己》一书,我通读了每一个字。他写得如此认真,我要读的对得住他。吸住了我的注意力的,不光是他的文字,还有被他的文字牵出来的我自己的记忆。他的文字温暖了尘封的往事,让复活的岁月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流动起来了。
我跳出来想,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神器?不错,读的是文字。然而,读的是文字吗?平凡黯淡如董华,高贵灿烂如卡夫卡,读他们读的是什么呢?无论文字的力量和荣耀多么悬殊,必有一个平等的支点为读者所用——我们读的终究是自己啊!灵魂固然是不可视的,透过阅读的文字,我却分明看见自己的灵魂跳上了一叶小舟,划走了。这里蕴藏的美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所以,董华的草木,也是我的草木。他的笔每碰到一样植物,我的眼前就移来一个放大镜,让我看到了叶片上的露水,甚至闻到了花朵的香气并隐约听到了虫鸣。这就是所谓大自然,亿万生物的无垠之海,人游在里面像一条鱼,极端渺小却无比惬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吗?在文字上滑行的灵魂告诉我,这股惬意之感千真万确,它像盛开的花朵一样真实。
读《白薯月令》,惊讶董华的熟谙农事,并立即想到了饥荒年的秋后,自己去刨捡落薯的情景。一块薯头都没捡着,塞了一口袋薯秧回家,将薯叶撸下来煮着吃了。读《温故香雪海》想到夜里偷偷爬树,读《椒乡八月》想到扎了手流血嘬血,读《黄花儿遍地香》想到百花山顶吓人一跳的花海,读《黑疸》想到跪在玉米地里锄草……于是再次跳出来断想,董华这本书的本质,是诉说人和草木的亲缘关系吧?那么,人和这些植物是什么关系呢?是人体热量与蛋白质以及叶绿素之类物质的转换关系吗?他罗列的草木林林总总,分为五辑66篇,不能入嘴的几乎没有。他用文字极尽赞美之能事,能扯多远就扯多远,最终却将它们近乎全部揪了回来,并一一吃掉了它们!
所谓人和草木的关系,一旦露出牙齿,本质也就露出来了。我们恨一个人恨到极点,常说老子要生吞了你。然而,爱一个人爱到高潮,也会忍不住叫嚣:让我吃了你吧!人对草木,终究是爱的。既入人口,便沦为肉身的一部分,这种爱至少从猿猴时代就萌芽,从树上爬下来之后便日益壮大起来了。董华赞美草木,大而言之是人类的基因作祟,小而言之,是代我们向生物链上的伙伴致敬。读者如果有心,尽可借助董华的文字,避一避人世的喧嚣,看一看那些沉默无言的生物之美。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人家的!
董华文字的意义,不仅仅含了这些。草木是个路标,一头指向了空间,在庞大混沌的空间里面,最清晰也最亲切的一个小地方名叫故乡;另一头指向了时间,在凌乱不堪的时间碎片里面,最难忘的是自家生命的刻度——那些被春夏秋冬埋葬了的平凡的日子。董华以草木为引子,催促周旋于世的身心踏上归乡之路,也将我们领回了葱茏的山水草木之间。那里有我们各自的家乡,是舍不下的生身之地,更是无法忘怀而徘徊不弃的精神家园。读者中不乏纯粹的城里人,或于董华津津乐道的这些草木无感。但是,我敢断定他的祖上和足下必有一条根须深深地扎在乡野的泥土之中。他必定是爱这些草木的,以生物基因图谱的广泛性来推断,他无疑是它们的亲戚,正如我们是无边草木的亲戚一样。董华以草木为知己,就是这个意思了吧?我读尽了他的文字,又涂抹了以上文字,无愧知己的知己了。坦率地说,人间的喜怒哀乐是如此之繁,可恶之人可厌之事又如此之多,口口声声的要爱草爱木,看上去是不是挺矫情挺做作的?不过且慢,当你静下心来,坐在山坡上,长时间凝视一棵小草和一朵无名小花的时候,你的灵魂一定是充盈而温暖的。那小小的植物是一个隐喻,它就是你!你的生命,你的人生,在茫茫的人海里面,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之中,你整个人呈现的就是这种淡然而坦然的样子啊!
董华是多么厚道的人,没有哪个作家像他这样喋喋不休又面面俱到地向草木们致以如此敬意。在喧嚣不已的时代,他这支朴素的笔尤显笨拙和不合时宜。但是,只要你我的心还有温度,必会感知他对脚下土地的忠诚,也必会感知他对同类的谦卑和善意。我们以阅读他平凡的文字向他致敬,继而透过这些文字向那些无声的草木致敬,进而向犹如草木一般的我们,向平凡而脆弱且孤独而又顽强的自己致敬吧。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年6月23日2版
人
非
草
木
亦为草木
《草木知己》
董华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草木知己》是作家董华创作的一部倾注真情,连接地气,书写中国北方草木的散文集。作者坚持创作数十年,将目光投注于其所生活的大地,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北方尤其是京郊地区的草木文化,不断挖掘和总结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以生动传神的笔触,将草木文化中本真质朴的篇章,予以生动的记录和呈现。
节选
白薯月令
白薯粉条
七月,白薯田一派美丽景象。
薯藤已经长长了,碧绿泱泱。有特色的薯种,比如“农大红一号”,它紫色藤上开花,开的花跟喇叭花一样。受了雨水,花朵向天空扬着,仿佛许多穿红兜肚的胖小子,抬着胖手,咕嘟着小嘴吹喇叭。农民珍惜土地,薯田边缘,或薯埂洼处,插种倭瓜。饥困时,倭瓜也当粮。倭瓜花开了,招蝈蝈,招马蜂,招蜗牛。全成为薯秧那胖小子的伙伴。
当下薯田的活茬儿,大项为翻薯秧。
翻薯秧这项活儿,是个人就能干。规则是把四向乱爬的薯藤做归拢,从左边翻到右边,让它们顺着一个方向爬。顺便清除野高粱、酸枣苗和侵夺白薯养分严重的杂草。
再个事儿,剪薯藤,筹集栽麦茬白薯。
栽种白薯,春天的叫“春白薯”,夏天的叫“麦茬白薯”。剪薯藤,要选长条,一根条剪几截,每截见个叶芽儿。栽法是一样的,只是不用多浇水。在雨中栽麦茬,更容易成活。
春薯生长期长,块儿大,“汗毛眼儿”(芽眼)少,用它育种不划算,浪费口粮。麦茬白薯形状细长,每块分量不大,但占数量。它的汗毛眼儿多,最适宜繁殖了。
温故香雪海
我说:洋槐花盛开时节,那就是“香雪海”。我青年时期农村生活的体验。
说它香,清幽的香气无可替代。那是天地孕育,又合于农民常性的一种清香,不温也不火,引嗅者心仪。谁若能把这种清香意味描述出来,定然是一位语言大师。处此间,只一树清香,还不会使你心旌摇荡;但如果千树万树的清香汇合起来,那可是强大的振奋力。十里闻香,说少了,数十里地范围内,都可以感受清香。
说它是雪,很合洋槐花体貌特征。摘下一串洋槐花详看,它斧钺形的花朵,绿萼部分包裹了亚黄颜色,由上部花唇到基部渐次加深。而从远处去看,尽呈着团团素白。有的洋槐树,花与叶同期,花也开,叶也生,而有的则花儿在先,几乎不着绿叶。花势繁茂,就像覆盖着春天的雪,形态美观。在没有月光之夜,一树树槐花堆拥的白,让你感到大街小巷里没有黑暗,篷门筚户充裕净朗。
关于对洋槐花海的钦仰,登高望远便知。你此时走上就近的山坡,抬眼四顾,就会觉出这真是一片槐花的海洋。观如海的槐花,兴许你也心胸如海。在滔滔花浪前沿还能看到些什么?我对你说,能看到浸润乡情的田畴、连接天际的绿茵茵的麦野。这时,最容易被田野景象感动:这是生养之乡、衣食之邦呀!
椒乡八月
椒乡——八月,忙中有乐,忙中有美。
忙是拳打脚踢的忙,乐是由心缝溢出的自然而然的乐。
从雨浇春开始,山里人就盼望着摘花椒时刻。它是一项大宗收入,也是日常吃油的依赖。看春雨浞湿了花椒树,一夜枝子泛绿,禁不住心头欢呼:哇,老天爷下票票儿啦!
经了春,经了夏,入了尾伏的风儿,刮来了花椒成熟麻麻酥酥儿的香气。
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山谷里的沟沟岔岔,一层层梯田的堰边,村口盘桓的山石路,凡长不起来其他果木的地方,都已降落了一顶顶红伞。倘若光华牵引住了路人,走近前,他会见老枝上红得酱紫,新枝上红得鲜艳。略微放眼,意象横生,一棵棵披红着绿的花椒树,像一群舞蹈的妙龄少女,轻盈的绿衣裙镶嵌着数不清的红玛瑙珠子。
——立秋风儿刮,快把椒篮挂!
秋风催促着农家准备功课,该用的大小篮子腾出来;挂钩,饮水罐儿找出来;做硬干粮的米面碾出来。最是当娘的心细,给在外的闺女、小子捎信儿:“快回来!”
——如期见着了儿女,老娘的脸笑开了花。
黄花儿遍地香
集菜名、草名于一身的黄花儿,在北京地区忒常见。
黄花儿喜于潮湿土地生长,花开为橙红色,或黄红色,由于黄色分量重,习惯上称“黄花儿”。
开花时节,一丛丛弯叶碧绿,细长叶子的腋芽间生出数枝花梃,每枝花梃上顶着有高有低几个花薹。刚生的花薹,简静,像小蚕蛹形状,风光在里边存着。过后,着了风,着了雨,炎热日头晒,花薹逐渐长大,花嘴逐渐裂开,从中闪出娇嫩的橙黄。经几日,人没注意,花就开大了。盛开的黄花,非常迷人,有纯朴村姑的笑靥之美。
黄花儿也迷恋人间,它的花不一堆开放,即便是数个花薹长在一枝,开花也分先后。这自然延长了观赏期。
赏黄花儿比较壮观,是于夏日高山草甸之上。高空白云飘浮,身旁凉风送爽,此间远望,青草芊芊,繁花遍野,郊原一派美景。似乎目眩神摇之际,一片片金黄夺了眼睛,那里的花势像一方方军阵,士气奔放;大山草甸莽莽沃沃,不见其阔,而是给它做了背景,愈发显示出了它性情的笃实和乐观开朗的力量……
黑疸
玉米在老庄稼人心目中,是虎虎实实、顶门壮户的小子。省心省力。当他们放下锄头,上坡打蒿草时,完全放心得下。玉米该怎样长就怎样长,吐花红线,灌浆,干皮儿,遵守着成长规律。
精壮劳力农事转移,离开大田以后,这时常奔玉米地去的,是拔猪食的孩子和上年岁的家庭妇女。玉米地里燥热,全选后半晌儿进地。拔着,拔着,偶尔一抬头,就看见那原本吐花红线的地方,结了一个大黑疸——玉米棵上边结的黑疸,裸露在外,一眼就能瞧见。满心欢喜,立即将它掰下放入篮儿里。
虽说是因为它影响了收成,但农家妇女不会过多联想,像男人那样生气。这跟她们平素习性有关:家里失去了大骡子大马见不到忒着急,而丢了一只鸡,则会心疼得哭天抹泪儿。
新掰下来的鲜嫩黑疸,外边包有一层光泽的灰膜,就像新鲜的猪、牛腱子肉一样外表光亮。切开它,白嫩嫩的植物肉体,嵌着黑点儿,那形体和黑点儿排布都跟火龙果差不离儿。当天采回的黑疸如果觉得够家里人吃上一顿,当晚就吃。切片,用荤油炒,嚼起来嘎巴嘎巴的,味道鲜美。按过去记忆,食味比现在的香菇要香,比小鸡炖蘑菇要美。
文字编辑:樊金凤
《文艺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每周一、三、五出版。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年9月25日,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
文艺报长按识别转载请注明:http://www.zhaigou365.net/szhj/12322.html